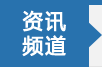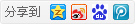為了陪來自剛果(金)的老鄉Tanya買貨,Felly起得比以往要早一些。3月14日的廣州清晨,室外溫度還不到20℃,Felly套上了他最喜歡的皮衣。
38歲的Felly經營一家跨國貿易公司已12年。辦公室位于小北附近一棟破舊大樓的17樓,只有一個文員在幫他處理事務。自2003年第一次到中國,Felly的家和公司就安在了廣州小北。
“小北——小非洲。當年小北比現在還要繁華,看到這里第一眼我就決定不走了。”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。
來中國之前,Felly在剛果(金)做外貿生意。“我去過很多國家考察。有一天家人跟我說,為什么不去中國看一看,給自己一個機會?”
此前,Felly的叔叔早于2003年已經到廣州做生意,收入還不錯。Felly追隨著叔叔的步伐來到廣州,一待14年。他如今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身份——剛果(金)在廣州的民間大使。
每個非洲國家在廣州都有一個民間大使,由在廣州的本國人選舉出來,對內負責處理糾紛、幫助本國人更好融入中國、舉辦社區活動等;對外要負責與當地的政府溝通。以剛果(金)的民間大使為例,這個職務一屆三年,2017年要重新選舉。
“選舉的會議應該安排在我們國家國慶(6月30日)之后。”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。政府部門一直希望民間大使能管理好在廣州的本國公民,此外他們還要承擔聯系和記錄同胞的數量。
“現在在廣州的剛果(金)人約500人。10年前,人數是現在的一倍多。”Felly說,2006年有1200多剛果(金)人在廣州。
Felly知道廣州剛果(金)人的大概人數,但廣州乃至廣東的非洲黑人人數到底有多少?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回答。
2017年3月,來自天津的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提交了一個提案——《建議國家從嚴從速全力以赴解決廣東省非洲黑人群居的問題》。提案中稱,據各方面大概統計(廣東)已有50萬“黑人口”,除合法入境者約2萬以外,其余為非法入境或過期居留,帶來一系列問題。
究竟“黑人口”人數幾何?2017年3月5日,針對外國人“三非”(非法居留、非法入境、非法就業)問題,廣州市公安局在官方微信號“平安廣州”上發布信息釋疑。據統計,2016年經廣州各口岸出入境外國人首次超過540萬人次,達到541萬人次。其中,入境的外國人269萬人次(含非洲國家人員28.6萬人次);出境的外國人272萬人次(含非洲國家人員29萬人次)。而非洲國家人員1.1萬多人,約占實有外國人總數14%。
Felly和Tanya是其中合法進入中國的非洲商人之二。
一
Tanya 7年前到華南農業大學讀研究生,如今在大連某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,但是她的生意并沒有離開廣州。休假的十幾天里,Tanya一直在廣州看貨,Felly陪同。
通常,Felly陪同逛街、介紹商家賣貨是要收服務費的,這是他公司眾多服務之一。
Felly和順德幾家家具廠的關系不錯。他近日接到非洲朋友發來的沙發照片,請他代為詢價。“沙發大概一萬多元,我可能會收幾個點的手續費。”不過,Felly沒有收Tanya的逛街“陪伴費”。
他帶Tanya去了流花市場。“流花市場很老了,是廣州最早的批發市場之一。”Felly說,位于廣州火車站附近的流花服裝批發市場開業于1996年,走的是外貿國際化的路線,多年來大量外國商人都聚集在此買貨。
穿梭在這里,Felly如魚得水。不管Tanya想買什么,Felly都能帶她快速地找到合適的店鋪。
走到流花批發市場中心區域的一家存活了十幾年的檔口,店里的員工紛紛和Felly打招呼。“Felly,你來啦?最近是名人啊,有那么多人找你?今天打算買什么?”
“我帶朋友來買褲子。”
“隨意挑,你知道價格的。”
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,一般他帶去檔口的客人,都會得到更優惠的價格。“而且,我不需要付定金。”這個“特殊待遇”足以讓Felly感到驕傲。
這里,一條男士休閑褲的價格在一百元左右。Felly說,這價位是質量比較好的,如果拿回非洲每條可以賣到兩百元左右。但是十年前,這兒同樣質量的貨物價格只要五六十元,賣出的價格不會比現在少太多。
“以前可以掙到百分之百甚至更多的利潤,現在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十幾。”Felly總結說。
Felly和Tanya看好的貨,通過空運寄回,一周之后就會出現在剛果(金)的市場上。Felly精于此道,他對界面新聞記者解釋,服裝是有流行期的,如果集裝箱送回國,一般需要一個月,衣服過季的風險很大。選擇空運只需一周左右。不過,以前空運32公斤的貨物運費不超過100美元,現在同樣重量的貨物空運需要170-200美元。
非洲大多數國家缺乏工業,物資匱乏,當地市場嚴重依賴進口。采訪中,有不少非洲商人這樣調侃,“如果中國人不賣衣服,我們可能都沒有衣服穿了。”
通過倒貨掙差價,幾乎是所有非洲商人共同的模式。此外,他們還會給在非洲的中國商人提供投資顧問、物流和倉儲等服務。
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主任梁玉成教授從2009年開始研究在穗非洲人的課題。他認為,在中國的非洲商人,承擔了經濟和文化橋梁的作用,但他們仍然只是族裔經濟,還是在非洲族裔內部的經濟體系中運行,并沒有完全融入中國社會。“進入我們勞動力市場,成為我們的勞動力的數量幾乎沒有。但是對中國經濟依然有好處。”

Felly陪Tanya挑選褲子。攝影:袁潯杰二
在穗非洲黑人的“廣州夢”,和貿易有關。
始于1957年春季,一年兩次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(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)即廣州交易會(下稱廣交會),讓“廣州貿易”聲名在外。
1990年代,廣東以出口導向型加工制造業的“世界工廠”聞名,本地工廠通過低勞動力成本為全世界生產各種便宜的貨物。
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成為貿易轉移的新契機,一方面東南亞各國經濟嚴重受挫,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崛起,廣東等沿海地區生產的貨物在非洲市場的份額越來越大。這是早期吸引大量非洲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主要原因。
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有關統計數據顯示,1995年-2002年是中非貿易的逐漸提升階段。在此期間,非洲對中國出口由24.6億美元上升至69.2億美元,非洲從中國進口由14.2億美元上升至54.3億美元。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商人告訴界面新聞記者,舊時利潤高,他們會找人拼單,湊貨物裝滿集裝箱或者選擇更快的空運。有時,寄一次貨物就能掙到一兩萬元,有的商人通過“倒貨”一年可以很輕松地賺一兩百萬元。
貿易形態催生了非洲人來廣州淘金的夢。
非洲人越來越多,廣州火車站附近的批發市場越來越旺,小北在非洲人心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。
廣東省的統計數據顯示,在穗的非洲人數量增速遠遠快于其他國籍人口增長速度。2000年在穗的非洲人口數量為6000人,2005年增長至20000人,年均增長率為33%。
人流帶動物流,帶來資金流。2003年起,中非貿易開始進入持續6年的快速發展階段。2003年-2008年,非洲對中國出口從83.6億美元躍升至559.7億美元,非洲從中國進口則由101.3億美元上升至510.9億美元。在此期間,非洲對中國貿易在2004-2006年以及2008年出現“順差”,其中2008年順差額最高達到48.8億美元。2008年是條分界線。
在國際金融危機等不利因素影響下,2008年-2014年,非洲經濟增速由2005年-2008年的5.83%下降到3.48%。
與此同時,中非貿易進入結構調整狀態。2008年中非貿易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。2009年,中國首次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并延續至今。
Felly的生意經歷了中非貿易關系的黃金年代,也見證了在穗非洲人口的急速增長。
2014年,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發布的《廣州外籍流動人口管理的現狀分與對策研究》指出,廣州已成為亞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。這些人主要集中在5個片區——小北、三元里、番禺、天河棠下和佛山黃岐。
小北是廣州最早的非洲人聚集區,所以在很多非洲人的心里,小北才是廣州的地標,有些人來到廣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小北的登峰賓館拍照留念。不僅是商人學生、游客,有些非洲的領導人千里迢迢到廣州也一定要去小北。2015年12月底,津巴布韋環境部長Muchinguri一行到廣州長隆參觀項目。下午活動結束后,Muchinguri的女兒點名要去小北買禮物,長隆安排了一輛車陪著Muchinguri在小北逛街。
非洲人的聚集區主要以小北路和下塘西路為核心,周圍幾公里的范圍都是非洲商人做生意的地方,這一帶也有大量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餐飲店。
在三元里,非洲人聚集區主要沿廣園西路兩側的批發市場、寫字樓組成。這里主要是尼日利亞人,很多尼日利亞人在這里開了檔口。
番禺的非洲人則主要集中在麗江花園和祈福新村附近,天河棠下和番禺情況類似,非洲人在此以居住為主。
佛山黃岐的情況比較特殊。在黃岐的非洲人也是以尼日利亞籍為主。由于黃岐地處廣佛交界,離廣園西路也不遠,早期一部分尼日利亞人為了節約生活成本住到黃岐,還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躲到兩個城市的交界處。
大量的非洲人搬去黃岐,源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帶來的治安工作要求。彼時,廣州對于“三非”人群的清查十分嚴格。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的李志剛教授在其所著的《廣州國際移民區的社會空間景觀》中提到:“非洲移民開始采取逃離廣州前往城市外圍區域的方式,尋求新的生存空間。”
2008年以后,居住在佛山的非洲人數量迅速增多。李志剛發現這些人群“大多屬于非法移民或經濟能力較低的移民”。
廣州市公安局2014年數據顯示,在廣州的尼日利亞人約2000人,是在穗非洲人數最多的。其中常住人口近300人。該國也是被遣送出境的“三非”人員主要來源國之一,最近幾年尼日利亞人有從廣州轉居佛山的趨勢。

Felly自己試衣服。攝影:袁潯杰三
今年26歲的Artan,來自索馬里蘭。他有一個醫生夢,“我從小就希望能幫助別人,覺得醫生是一個不需要自己有很多錢,就可以幫助別人的工作。”
高中畢業后,Artan開始考慮留學的事情。他意識到,學醫最好還是出國,非洲的醫療水平太差。“我考慮留學的國家有兩個條件,第一是醫療水平要比我們好,第二是學費家里能負擔得起。中國正好兩個都符合。”Artan說,在索馬里蘭有一些中國商人從事礦產生意,他所了解的中國,都是索馬里蘭在中國留學的朋友告訴他的。在朋友的口中,“中國很好,一定要去看看。”
Artan第一次到中國的落腳點是武漢。他現在是暨南大學醫學院的學生,2017年是他在中國的第7個年頭。
在武漢讀大學時Artan已經來過好幾次廣州。“我在小北有很多朋友,他們叫小北‘小非洲’,我也喜歡把小北稱為‘小非洲’。”
每年放假Artan回到索馬里蘭,都有很多人問他關于中國的情況。“我們那還有很多人希望來中國留學,但是現在中國的簽證政策變了,想來留學很難。他們只能等。”
2013年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》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》(下稱新移民法)實施,管理趨嚴。外國人在中國生活,除了要有護照和簽證外,還要隨身攜帶居住證明。這幾年在小北周邊的小區,還能看到社區貼的提示,提醒外國人要隨身攜帶相關證件,供警察查驗。
由此帶來對策的變化。有在穗非洲人表示,他們盡量減少用護照登記,這樣警察就不容易追查到。一旦簽證到期了被抓到遣送回國,就很難再回到中國了。
此外,界面新聞記者了解到,不少在穗非法停留的非洲人為了避免用護照登記被追查到,會和地下錢莊進行非法的交易。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表示,有些地下錢莊就躲在寫字樓里,但是沒有熟人引領很難了解到情況,“而且你并不是非洲人。”
非洲人為了留在中國做生意而取得合法身份,也愿意付出昂貴的代價。一般外國人來經商,需要中國的公司開邀請函。現在一張邀請函的價格最高已經被炒到兩三千美元。
“我們的簽證制度對于他們來說,過于嚴苛。當年我向監管部門提了相關建議,后來他們也有所改動。警方在執法時,就把非法移民分為惡意和非惡意,短期的非法滯留交罰款就可以了,不再像以前可能幾年無法入境。”梁玉成說。
梁玉成告訴界面新聞記者,他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非法移民,來中國的前兩三年是有合法身份的。
新移民法實施后,希望獲得續簽的商人必須先離開中國回到非洲,成本上升,獲得續簽的風險也提高了。當他們在中國的生意穩定后,有些人就干脆冒著法律風險“黑”在中國。
四
2008年,梁玉成去英國參加聯合國會議,討論的話題是50年以后的全球移民問題。
梁玉成說,長期以來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數量,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輸出國,極大緩解了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問題。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,當時的中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,50年以后將進入老齡化社會,需要大量輸入年輕人口,將和其他發達國家去世界上“搶”年輕人。
“這次會議對我有很大的啟發。按照人口學的推演,中國有一天將會不得不引入移民,所以我覺得可預先做一些研究。”梁玉成回憶道。
2008年大量的非洲人已經開始在廣州聚集,所以梁玉成采用受訪者驅動抽樣方法研究這個問題。“這個方法專門研究隱藏群體和稀少群體,對這些群體進行抽樣和大規模調查。在我的受訪者中,近一半是非法居留的非洲人。”
2010年之前,從廣州搬到黃岐的非洲人住在更靠近廣州的江濱大道、黃岐步行街周邊。但2010年廣州亞運會后,佛山響應廣州號召,也開始加強清查力度,并對非洲移民的小區進行頻繁搜查。
李志剛指出,2010年中旬,大量的非洲移民離開佛山,為了避開警察,持有居留許可證的非洲移民則選擇遠離,去更隱秘的城中村居住。
2010年后,在黃岐,非洲人的聚集區躲進兩公里外的北村和中村這兩個城中村里。
但這并不是這些非洲人最終的落腳點。
2012年深圳大運會、2013年新移民法的實施、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的肆虐,每次大事件發生,相當一部分在穗非洲人都會更小心地躲藏起來。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人告訴界面新聞記者,他知道同胞里有一些非法移民。“在不同的時候,被警察攔截的風險不同,通常凌晨、深夜以及午飯時間,是最安全的時候,此時警察少。”所以很多人選擇早出晚歸。
從2008年開始在黃岐開出租車的袁師傅經常搭載黑人乘客,他回憶稱,“沒有身份(簽證)的非洲人是不敢坐公交和地鐵的,他們一般三四個人拼一臺出租車。早上從黃岐去廣園西路,晚上九十點鐘再回來。廣園西路離黃岐不遠,打車不會超過30元。”
晚上10點的黃岐鎮泌沖村,非洲黑人的身影在街上逐漸增多。他們也經常在岐海苑對面的大排檔吃夜宵喝啤酒。
根據梁玉成的研究,在2010年前后,在穗非洲人數量達到了近年來最高峰,估計當時的數量約有5萬人(包括合法和非法居留人數),但是他沒有透露合法與非法居留人數具體比例。在穗的非洲人中尼日利亞人占比最高,尼日利亞人中主要是伊博族人。
伊博族是尼日利亞人數最多的民族,他們曾經想獨立(比夫拉戰爭)但失敗了,損失慘重。伊博人在其國內沒有政治主導權,被趕到貧瘠的山區。但是伊博人很聰明,被稱為“非洲的猶太人”,他們在全世界尋找商機做生意,大量遷居國外。
2010年前后,有專家統計在穗非洲人數量約為2.5萬人(合法居留)。梁玉成告訴界面新聞記者,也正是這個2.5萬的數字成為后來大家誤解在穗非洲人數量的主要依據。因為按照發達國家社會學統計的算法,總移民數等于合法移民數乘以8。所以當年有研究者用2.5萬乘以8,得出在穗非洲人總共有20萬人,也對媒體說了這個數字。
“但是這種統計方法計算,忽略了中國的國情。因為中國的警察相較于西方警察,執法權更大。比如,美國的非法移民走在街頭,如果沒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,但是在中國是可以的,所以中國的情況絕對不能乘以8。”梁玉成認為,這些年由于監管更為嚴格,出現了非法移民郊區化的情況。
非法移民一般就躲到周邊的城市,或者城市監管的死角地帶。廣州是合法為主,佛山是非法為主,這種情況不光廣州有,北京也有,很多非法移民居住在望京。非法移民呈現大分散、小聚集的現狀。

一到晚上,登峰賓館門口人口攢動,這是大家認識朋友,交流信息的好地方。攝影:袁潯杰五
在穗非洲黑人的“廣州夢”能否延續下去,和經濟有關。
2014年,中非貿易迎來歷史新高,中國海關數據顯示,2014年中國與非洲貿易額首次突破2200億美元,同比增長5.5%。
但是2015年開始,基于非洲政治局勢的動蕩與石油價格的變化,中非間貿易額下降。很多非洲商人即使冒著違法的風險,也不愿意回國。
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,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經濟增長率持續下滑。2016年,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實際GDP增長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表現最弱的,這主要是因為占地區GDP整體規模一半以上的兩個最大經濟體——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表現不佳。石油價格大幅下跌,是造成尼日利亞當時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因素。
2015年中國與非洲貿易額為1790億美元,同比下滑19.2%;2016年中國與非洲貿易額為1491.2億美元,同比下降16.6%。
從2014年廣州政府公布的數據來看,在穗的非洲人數量明顯減少。數據顯示,2014年,廣州市居住外國人士11.8萬人,常住6個月以上有4.7萬人,臨時來穗7.1萬人。其中來自非洲國家的占14%,約1.6萬人。
廣州公安提供的數據顯示,2016年廣州市公安機關查處的“三非”外國人占來穗外國人總數的0.11%,其中非洲國家人員僅占18.9%;以2015年為例,廣州警方共查處的“三非”外國人僅約占外國人總數的0.15%,其中42.7%為疏忽大意造成的輕微非法居留(10日以內)。通過深入治理,在穗外國人“三非”問題持續好轉,自2015年開始,“三非”問題查處總量連續2年下降,特別是2016年查處人數同比大幅減少20.7%。
界面新聞記者發現,雖然2016年在穗非洲人數量比2014年少了5000多人,但是在穗非洲人數量占在穗外國人數量比例不變,仍然是14%。
有專家分析稱,這說明在穗的外國人數量整體在減少,并不單單是非洲黑人的減少,主要還是跟政府的簽證政策與國內經濟轉型有關。
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,從2014年前后就有很多人離開中國去其他地方找商機。他也曾猶豫過要不要離開中國,回家鄉重新開始。但最近發現情況又變了,“廣州夢”仍可繼續,“我晚上去登峰賓館,發現最近突然又有不少非洲人來了。應該又有新的商機。”
梁玉成分析稱,首先,整個非洲政治經濟出現問題。在金融危機之后,由于非洲經濟不景氣,移民數量開始減少。其次,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,輕工業開始轉型外移,許多非洲移民跟著產業的轉移而轉移。在多種原因的作用下,現在在穗非洲人最多不超過3萬人(包括合法居留和非法居留)。
梁玉成說,目前若能使非洲移民問題可控,從中國對非洲戰略層面來說,一帶一路、國際化方面,都是有好處的。
“國內工業產能過剩,所以需要將過剩的產能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輸出。從這個層面上來說,我們需要非洲。另外非洲有我們所需的大量的原材料,將來也是我們的市場。”梁玉成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