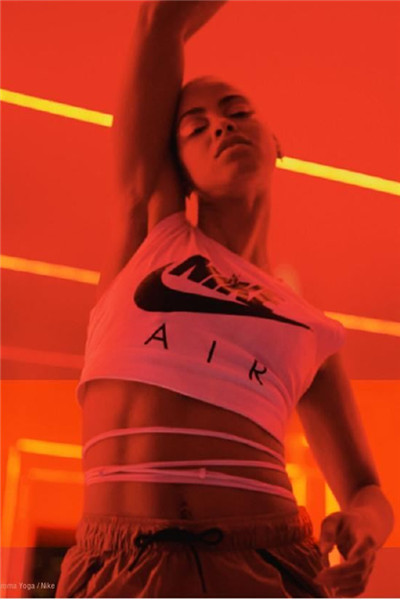其次,有了公檢的質量指標,也就是有了大家認可的價格,這個合作機制就可以說話了。“如果你缺錢,我可以融資給你。比如,你這批生絲進入了我們的中心,檢測結果是5A的,市場價格如是40萬,10噸就是400萬。按7折算,280萬你先拿去用。這部分絲就放在我這里了。對于綢廠來說,要買這10噸絲,手上沒有足夠的錢,但這不要緊,算好價錢我讓你先拿去用,只是不能全部拿走,可以用一點,拿一點。所以你只帶很少的錢,就可以拿到這批絲了。”這就是利益上的好處。
“非常佩服凌董的智慧,如果這個計劃能夠順利推進,我們纖檢所一定積極爭取生絲的公檢數量,助推湖州繭絲綢產業發展。”陪同記者采訪的湖州纖檢所副所長邢秋明插話道。
凌蘭芳笑著說:“下個月就開工建設,計劃到明年全部落成。檢測是這個中心的核心鏈條,技術規范是必定要的。”
轉型升級,背負著絲綢的希望
“我17歲做絲綢,當時沒夢想,只想著活命。開始時非常艱難,但內心確有絲綢情結。”凌蘭芳回憶過去的歲月很是感慨。“10年前,這里五大綢廠倒閉,真有‘哀鴻遍野’的感覺。經過10年的發展,我們站起來了。”
站起來不假,但如何站立長久且站得很直,是這位絲綢行業領軍者考慮最多的。凌蘭芳說,絲綢之路集團早在兩年前就開始提出轉型升級、破難創新的戰略突圍了。
必須轉型升級的道理在于:“改革開放初期,短缺經濟讓紡織業掘到第一桶金,低成本資源、低水平管理、生產低檔次產品去滿足低價格需求,現在完全倒過來了,路徑依賴行不通,需要去適應的是我們自身。轉型升級政府是主導,企業是主體,市場是主旨,位置必須擺正。”凌蘭芳這樣闡述。
凌蘭芳認為,轉型升級的最終出路是7個方面:一是蠶桑產業化;二是繅絲智能化;三是制造無梭化,就是要數碼化;四是后整理精美化;五是市場內需化;六是產業要重組;七是品牌國際化。絲綢之路集團由此制定了產業鏈升級路線圖:制絲前道提升,織造中間突破,品牌終端拉動。然后,自從美債歐債危機相繼而來,與國內經濟盤整疊加,紡織制造業步入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困難時期,絲綢行業作為傳統制造
業生存發展的壓力更大,轉型升級的任務更重。凌蘭芳在各種場合大聲疾呼要給紡織民企減負、減壓、減稅,要求政府支持紡織民企破難創新,其中也談到過絲綢行業的種種困難。
2012年8月15日,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嘉興召集部分企業家開座談會,凌蘭芳是第一位發言者,他匯報了絲綢紡織行業情況,提出“不轉型升級和自主創新就是等死”的見解。溫總理當場關照,讓有關部門一起考慮一下,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給予扶持和幫助,加快產業轉型升級,促進行業健康發展。
轉型升級的最終目的是提高絲綢產品的品質和提高生產效率,而產品質量是品質的核心。在集團內部,凌蘭芳不厭其煩地講轉型升級和質量的重要性。“細節決定成敗,質量決定未來。”這是凌蘭芳常說的話。
今年6月,集團召開繭絲綢市場形勢交流分析會,凌蘭芳強調要堅定不移地牢記質量,而且借助具體分析形勢闡述轉型升級的道理。“價格分化到什么程度了?好絲和差絲差到了一半。1噸好絲到了50萬以上,差絲卻在40萬以下。這個價格差,比我們以前的預計要大。這告訴我們,經營的大趨勢就是高質量,質量是關鍵。”
凌蘭芳還深入淺出地說:“今天你因為提高質量多賣了1塊錢,這1塊錢可能是你投入了5塊錢換來的,那么你要堅持住,提高你的工藝開發、研發創意、工藝水平和技術操作,總有一天會逆轉,你投入1塊錢,換回的是5塊錢了。這個就是抓質量、抓品牌的關鍵,大家一定要牢記。往往一試二試的時候,道理說得清;三試的時候,有點吃不消;到了五試的時候,覺得虧多了,不干了,趕緊逃出來。接下去發生了什么?贏利的那天卻因為你的放棄而與你擦肩而過。所以堅持和堅守很重要。”正是基于這一發展戰略,絲綢之路集團自2005年起實施了一系列“大動作”:斥資1.5億元建設菱湖絲綢工業園,使企業整體“脫胎換骨”;把絲綢制造的前道工序轉移到原料和勞動力都比較豐富的廣西、四川等地,建立生產基地;大力推進技術改造,引進國際先進設備;設立家紡公司,開發推出“歡莎”系列高端家紡產品,直接進入家紡終端產品領域……
凌蘭芳決定走高端差異化路線;生絲做品位,綢緞做品質,家紡做品牌。建立優質資源基地,導入先進管理體系,樹立頂級終端品牌。如此種種,不僅使企業形成了從制絲到面料,直至服裝、家紡的完整產業鏈,而且逐步實現了繅絲智能化、織造無梭化,走上服裝品牌化、家紡國際化之路。
作為領軍人物,凌蘭芳經常在業內闡述:轉型升級是21世紀上半葉中國制造業的一個偉大歷程,明智的絲綢企業一定會在這個機遇期迎來事業的創新發展。同時他提醒,“轉型升級實際上是我們民營企業在新形勢新局面下的適應性轉變,是一次脫胎換骨和浴火重生,是做大做強的最后機遇。”
為此,凌蘭芳讓每個絲綢之路人都知曉了這四句話:“轉型升級,生死時速,破難創新,風雨兼程。”